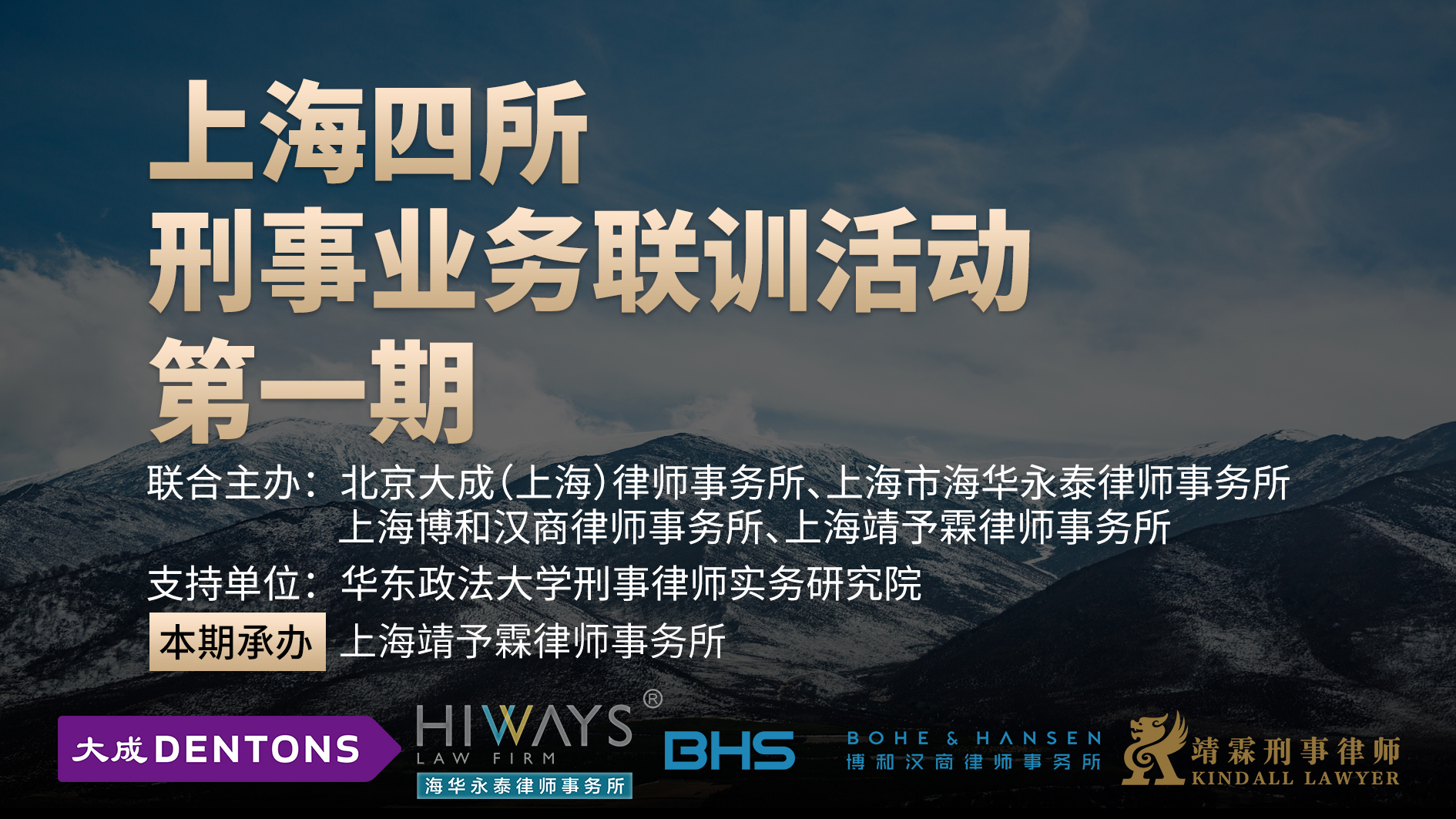主题:《虚假诉讼罪的实务研究——以控告为视角》
主讲人:王超强
时间:2021年9月29日18:00
地点: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会议室
本期主持:王玺

2021年9月29日晚,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第177期刑辩道场准时举行,由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王超强主讲《虚假诉讼罪的实务研究——以控告为视角》。
首先,王超强书记从虚假诉讼罪的基本理论入手,讲解了对该罪条文中“捏造”的理解。根据“捏造”的程度进行分类,“捏造的事实”可分为完全捏造(纯属虚构、无中生有型)、部分篡改(部分篡改型)、串通诉构(偷梁换柱型);根据“捏造”的主体和查处的难度进行分类,“捏造的事实”也可分为自己捏造、伙同捏造、利用他人捏造。“捏造”的类型可以分为纯正的捏造、不纯正的捏造、隐瞒事实和恶意串通,骗取法律裁判文书。对“捏造”的实践衡量和把握,可以总结为三个要点:第一,无中生有型和部分篡改型的“捏造”,具有同等危害性的,均应纳入刑法评价范围;第二,捏造的事实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对这样的虚假性的诉讼,也应当纳入虚假诉讼罪进行评价;第三,对于“合法权益”的判断,不应当仅限于财产权益。

其次,王书记列举了五个不同类型的虚假诉讼案例,结合法理和实务经验,为我们深入分析了虚假诉讼罪的实务难点和要点。根据这些案例,他指出,如何在虚假诉讼的控告中寻找证据,不仅需要一定的技巧,还要有一定的耐心,通常来说,虚假诉讼罪的控告业务的难度远大于该罪的辩护业务。
再次,王书记为我们分享了关于虚假诉讼罪的控告经验,他认为,突破该罪控告难的问题,可以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对无中生有型虚假诉讼应有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有必要肯定极致的限缩解释的积极作用,即把无中生有型作为唯一的构罪类型,也要批判极致的限缩解释,因为这种做法产生的弊端是“挂一漏万”,容易发生巨大的犯罪黑数,导致大量虚假诉讼犯罪得不到司法打击,被害人的权益无法获得救济;第二,肯定恶意串通、偷梁换柱型虚假诉讼构罪说,对该种类型,在本质上等同于无中生有型虚假诉讼;第三,针对同一被害人的多起虚假诉讼,在构罪标准上,应当算细账,而不应算总账;第四,对于部分篡改型的虚假诉讼,应当根据篡改的虚假数额进行区分,可以参照职务侵占罪或贪腐犯罪的构罪标准。

最佳点评人

讲座结束后,在场律师都借此机会,纷纷将自己办理虚假诉讼案件中遇到的实务问题,向王超强书记请教。其中,杨晓明律师提出的问题,引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拓展了本次讲座的主题和视野,被评为最佳点评人。
与谈人

李贺超谈了三点感受:
第一,当事人大意。在资金周转时本应有足够的证据留存意识,但遗憾的是很多当事人没有注意到证据的留存,从而埋下隐患,陷入他人虚假诉讼的套路中,企业及相关人员应当充分重视律师的作用,排除风险于微时。
第二,法院强势。在实务中,虚假诉讼罪的控告难,主要原因在于办案机关对刑民交叉案件定性把握不准确,以及法院对自身既判力的维护。其实虚假诉讼人为创造或滥用了诉权,不但极大破坏了诚实信用的社会秩序,也破坏了法院的审判秩序,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基于受欺骗所作出的判决形成的既判力,相比法院审判活动的自我修正,二者要达到平衡,还有赖于立法司法人员认识的不断更新。
第三,律师办案难。在虚假诉讼罪的控告案件中,对方行为人操作手段高明,公安立案动力不是很足,增加了控告的难度。在辩护案件中,由于极致限缩解释的原因,留给辩护人更改定性的空间不大。但无论是控告案件还是辩护案件,要把握“部分篡改”的理论为我所用,律师应该学会更深入的阐释罪名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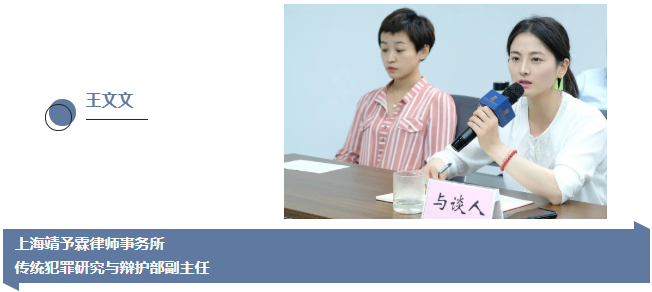
王文文律师提出了一个案例,两个业务方向,和三点感想。
首先,结合本次主题,她分享了自己参与办理的一起控告案件。
其次,根据该案件,她发表了两个关于虚假诉讼罪业务方向的看法:第一,在虚假诉讼的案件中,我们的客户可能更多的是控告方向,正如超强书记所言,辩护类的虚假诉讼案件通常证据比较扎实,可辩空间较小。实践中大家可能也确实会遇到控告案件更多;第二,刚才的案例能够看出企业客户在商业活动中存在很多没有关注的风险,律师就可以为他们做好这种风险防范,包括财务结算、股权变更时的责任承担、并购尽职调查等等,有刑事律师的参与能够更好地预见这些风险。
最后,她表达了三点感想:第一,在办理虚假诉讼控告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多借助其他机关的力量办案,例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对民事诉讼有监督职责,有检察院等监督,法院在审理相关民事案件的过程中会更谨慎。第二,我们也要注意自身的职业风险防范,关注到icourt的一份大数据报告,50起虚假诉讼案件中会有5个律师涉案,虽然我们只做刑事业务,可能涉及虚假诉讼的情况少,但有这种意识还是有必要。第三,当存在虚假诉讼和诈骗的竞合时,以诈骗罪进行控告有时更有利于立案。
总点评人

郑凯方律师认为,虚假诉讼罪高发,但实务判例并不多。虽然司法机关一再强调要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但实际上启动虚假诉讼刑事程序的案件很少,而且启动困难重重,这既有该罪名证据收集困难的原因,也与实务中对虚假诉讼作出的严格限缩解释是分不开。
她提出,严格的限缩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民事诉讼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如果将民事诉讼中存在的虚假成分、隐瞒真相都纳入虚假诉讼范畴的话,一方面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另一方面也会对民事诉讼秩序、法院审判的公信力等造成负面的影响。可以考虑引入比例原则,根据严重程度判断是否构罪,但这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
郑律师认为,严格的限缩解释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有利于我们的辩护业务,坏事是不利于我们的控告业务。但无论是控告还是辩护,都要掌握虚假诉讼罪理论的精髓,融会贯通。她结合自己处理的多起虚假诉讼控告案件,进一步分享了三点控告经验。
法律适用方面,一要理解什么是“无中生有”,进行适当的扩大解释。例如,改变资金性质,将本不属于借贷关系的往来款捏造为借贷关系,是否属于无中生有?二要活用此罪与彼罪,尤其是诈骗罪与虚假诉讼罪,根据司法机关的态度,合理选择以何种罪名控告。三是选择民事诉讼还是刑事控告途径维权,从而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需提前为当事人做全面分析不同程序的利弊,并根据走势调整策略。
证据收集方面,应当有善于发现矛盾、发现漏洞的眼睛,抓住诉讼过程中对方的问题。由于收集对方恶意串通的证据较难,所以“巧取证”尤为重要。
程序选择方面,公安机关直接介入民事诉讼的难度很大(尤其是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最便捷的控告方式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争取法院直接移送案件,民事转刑事。同时,随着检察机关监督权不断强化,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进行控告申诉,也是好途径。
作者: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靖霖刑事律师机构副主席 王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