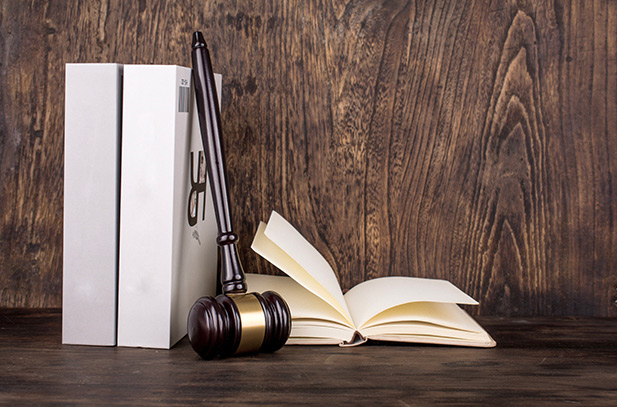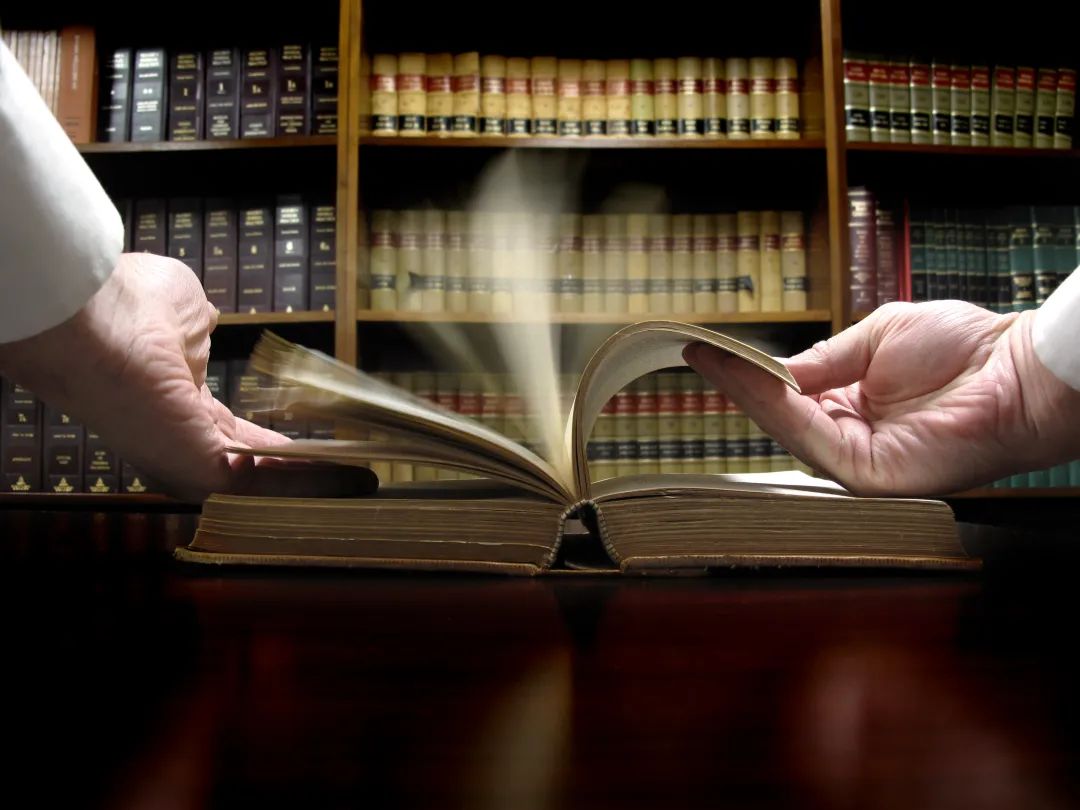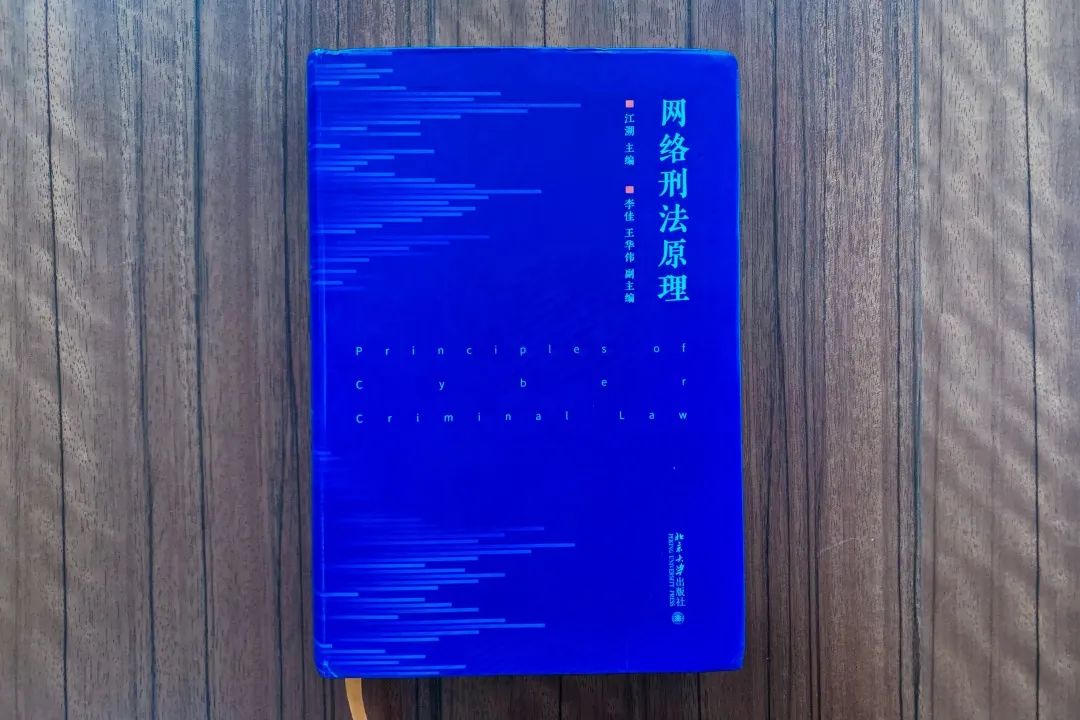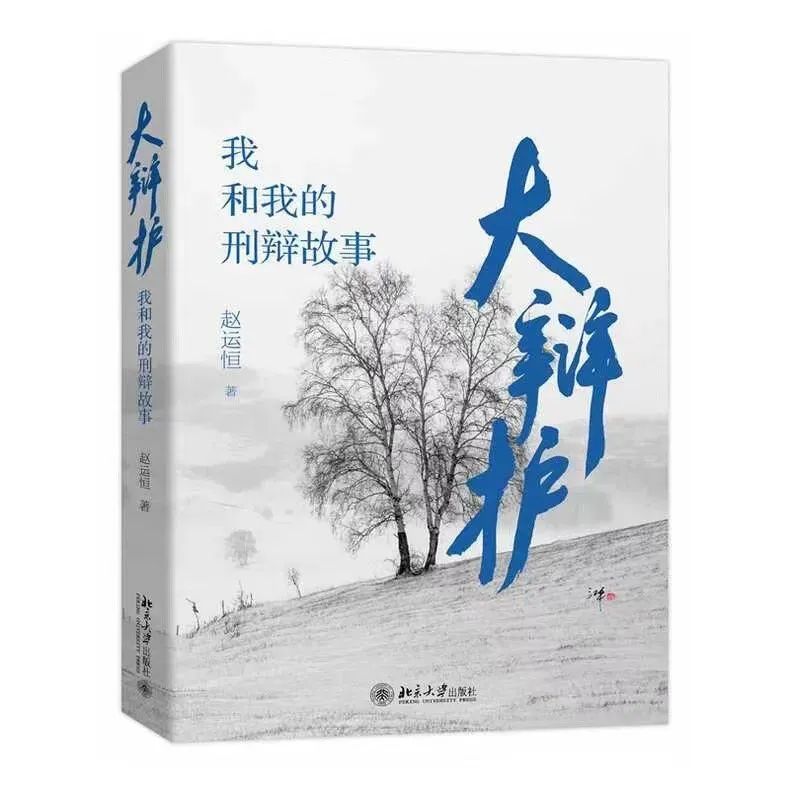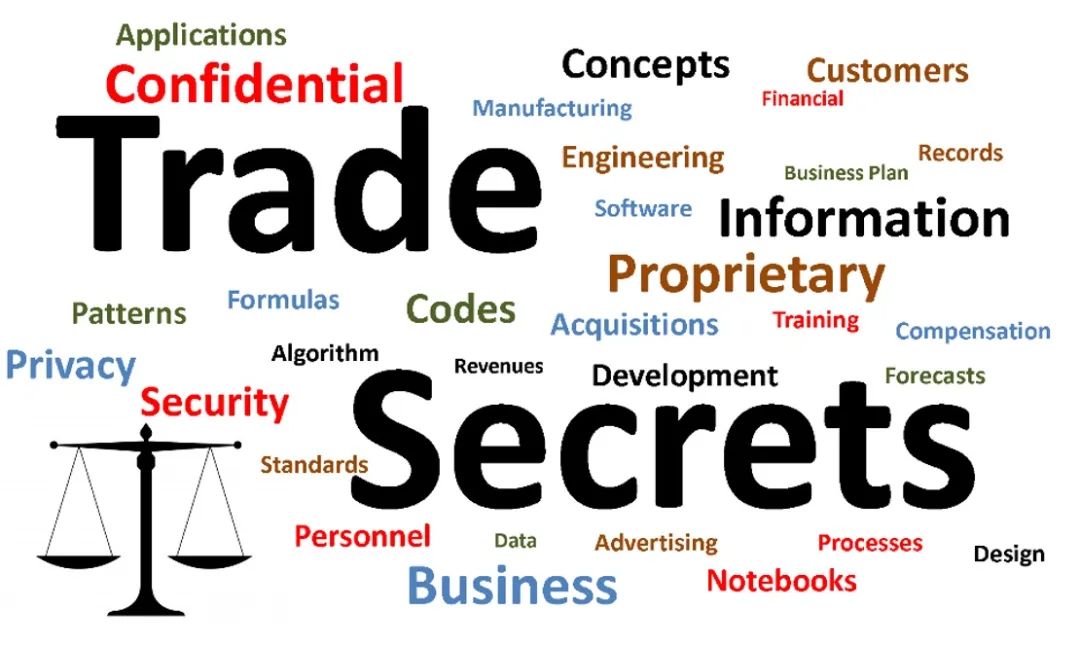5月18日上午10时至11时30分,由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孙宇为大家主讲《非法集资案件中涉刑资产处置问题探索》,在腾讯会议线上如期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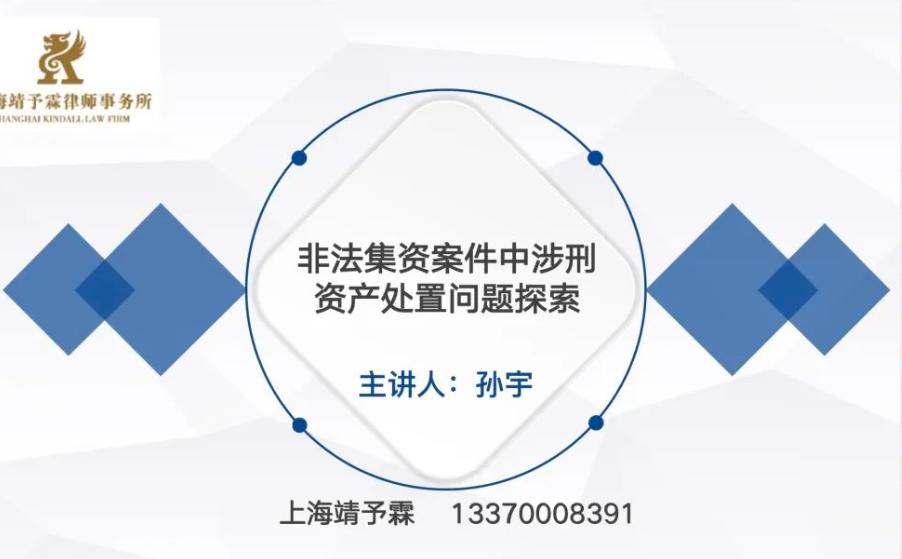
一、法律适用复杂
涉刑资产处置中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十分复杂,主要体现于三方面: (一)涉案资产范围认定不清晰。非法集资案件中,涉案公司的资产众多,少则数千万多则数百亿。这些资产并非全部在涉案公司名下,有的会由关联公司或实控公司掌控,将涉案资金投资到了众多项目中。有时关联公司与涉案公司的关系不明确,并未进行工商登记,而是通过股权代持协议来体现,通过控制关联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网银秘钥等手段,实际掌控关联公司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关联公司的股权及名下资产,也时常存在第三人的他项权利,这又加剧了涉案资产认定与处置难度。 (二)刑事判决表述不清晰。由于非法集资涉案公司经营模式复杂,涉案资产众多,侦查机关很难厘清资产情况,遂在侦查之初查封、冻结、扣押的范围极易扩大,有时在集资参与人追赃挽损的压力下对于权属不清的资产一查了之。在审查起诉环节,检察机关多重视犯罪嫌疑人的定性、量刑问题,鲜少会对涉案资产进行处置。到了最终审判环节,大多数审判机关在判决书中不会明确涉案资产的范围、涉案资产如何处置,大多笼统地写“在案扣押、冻结款项分别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实践中仅有少量判决书中阐明了哪些资产属于赃款赃物,并发还给集资参与人。 (三)交叉问题法律适用不清晰。有的涉案资产本身权属不清,又存在刑民交叉或刑行交叉问题,这些交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本就存在争议,导致涉案资产更加难以处置。其中刑行交叉的情况较为少见,刑民交叉则比较常见。此外,由于承办法官长期处理刑事案件,缺乏全面、整体的法律思维,很难想到刑事程序中的某一行为会对民事、商事、甚至是破产程序产生何种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是由于承办人员缺乏对刑事案件的全面、深入地思考,导致了案件承办人在面对交叉问题时消极处理的态度,大多本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处理案件。 二、不同主体利益诉求冲突 (一)集资参与人维权难、维权成本高。一方面,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集资参与人诉讼权利受限,没有合适的渠道了解基本案情、案件办理情况,即便聘请了专业的代理律师,律师也无法阅卷无法发现财产线索。集资参与人维权无门后便通过上门、上访、上街等方式维权,企图引起相关职能部门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非法集资案件办理周期长,集资参与人挽损比例较低,而聘请专业律师花费较高,维权的成本较高,而未来挽回损失又存在种种不确定。 (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也存在种种利益冲突。一方面,对中下层员工来说,非法集资案件的未兑付金额往往特别巨大,这些资金缺口要么是实控人转移、挥霍所致,要么是投资项目失败、借款人逃废债等因素造成。此时责令中下层员工退赔并承担连带责任,甚至终生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是有违公平的。另一方面,对实控人、高管来说,办案机关因投资人施加的压力,查、冻、扣的资产呈现扩大化趋势。但凡认为与案件存在联系的,往往会一查了之,而涉案资产一旦被查、冻、扣,将长期受限,难以进行变现、抵押、商业运作,到了法院执行阶段多需要折价拍卖用于兑付,不仅不利于集资参与人最大限度挽回损失,也损害了财产权利人合法权益。 (三)对案外人、利害关系人而言,办案机关扩大查封范围,延长查、冻、扣期限,时常侵害案外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加之案外人、利害关系人没有途径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中,诉讼权利缺失。一旦资产被查、冻、扣,案外人、利害关系人不得不被迫面临资产被查、冻、扣后的连环不良反应,如资产无法抵押、运作,成为不良资产面临贬值,依靠资产运营的企业甚至会破产。 三、办案机关主观能动性较低

造成办案机关主观能动性低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涉众型案件较为敏感。非法集资案件因集资参与人众多,少则数百人多则几万、几十万人,属于涉众型案件。集资参与人因维权往往会形成小团体,不断通过信访途径持续给办案机关带来较大的压力。鉴于缺少有效途径挽回损失,集资参与人施加的压力促使办案机关只能通过扩大涉案人员范围,大范围地查封、冻结、扣押资产,来平息集资参与人的“怒火”。于是,实践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以下局面:一是办案机关尽量多地抓捕犯罪嫌疑人,查封后却没有时间、精力和专业能力来处置、运作、变现这些资产;二是有时间与精力的集资参与人没有权利处置被查、冻、扣的资产,只能被动等待分配;三是有动力、有能力来处置资产的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无法有效处置资产。因此形成了资产被查、冻、扣长期无法、无人处置,随着时间的推移、诉讼程序的推进,时常出现涉案资产处置就不了了之的僵局。 第二,办案机关工作量大,出力不讨好。办案机关办理非法集资案件需要完成大量调查取证、做笔录、外地出差、梳理分析等工作。即使这样,集资参与人可能还会因难以挽回损失表达种种不满意的情绪。又因涉众案件中,难免会出现极端的集资参与人,对于办案机关而言,可谓是不管案件办好办坏,总归有人不满意,出现出力不讨好的情况。 第三,法律问题复杂,自身能力不足。基层侦查机关承办案件量大,即使是较为专业的经侦部门,面对复杂疑难的非法集资案件,以及案件背后的复杂交叉法律关系、资本运作逻辑、商业惯例等问题时,很难有积极性去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研究错综复杂的法律、资本、商业等问题。 第四,本位主义较重,以不出错为目标。在本位主义的影响下,侦查机关认为其职责范围就是查明犯罪事实,固定犯罪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查扣冻涉刑资产,至于后续如何处置资产则并非其职责所在。检察机关认为其负责法律定性、法律适用,也不愿主动干预、插手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的工作。虽然相关司法解释要求审判机关有责任在一审宣判前做好资产处置分配方案,但实践中大部分法院依旧没有对涉案的资产如何处置予以明确。综上,非法集资案件给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集资参与人、案外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感觉是,公检法都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按照最“保守”的方式,谨小慎微地办理非法集资案件,生怕哪方面出现瑕疵被集资参与人“盯上”、“揪住”。
四、资产处置推进难 首先,刑事案件经手的办理机关多。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到审判机关就经历了三个办案部门,若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案件还需经历二审裁判。上述办案机关面对敏感的涉众型案件,本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按部就班地推进诉讼流程,遇到重大、疑难、复杂的交叉问题,本能地推给后一道程序处理,鲜少在诉讼中积极处置资产,最终全部堆积到了一审法院的执行部门。 其次,刑事案件诉讼程序长。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从立案到判决生效,短则需要半年左右,长则需要1至2年才能审结。非法集资案件更甚,从刑事立案到最终的分配环节,大多需要4年以上的时间。若侦查机关分批处理犯罪嫌疑人,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在逃的,那么办案所需的时间会更久。 最后,执行环节障碍多。一是刑事财产性执行中因为没有顾及某一方的利益,尤其是广大集资参与人的利益,如追赃挽损比例低,容易导致发生维稳事件,引发社会问题。二是涉案公司通过代持协议、实际控制等方式获取资产控制权,有的甚至没有签订代持协议或代持协议不完善,早期侦查阶段查、冻、扣就有争议,若干年后的执行势必导致被执行人的不配合。三是案外人、利害关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执行异议、信访等方式给办案机关尤其是执行部门施加压力,客观上也会拖慢资产处置的进程,如涉案不动产有长期租约未到期、存在他项权等。四是涉案资产因民事、刑事案件被查、冻、扣。涉案公司资金链断裂后,涉案公司名下或控制的资产很快面临一系列的民事诉讼、仲裁,进而被民事法院查、冻、扣。此外,若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出现其他刑事问题,被异地侦查机关刑事立案,也面临着被刑事额查、冻、扣。上述民事、刑事问题又加剧了执行环节的难度。 五、案例解析 最后,孙主任通过六个案例,从涉案公司、案外人、利害关系人三个不同视角,深入讲解了非法集资案件中涉刑资产处置案件的问题、难点、痛点,并结合办案的经验、教训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在场律师、法律工作者对此类业务有了感性认识,为以后办理非法集资案件打开了思路,为律师、法律工作者开拓涉刑资产处置这片蓝海业务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