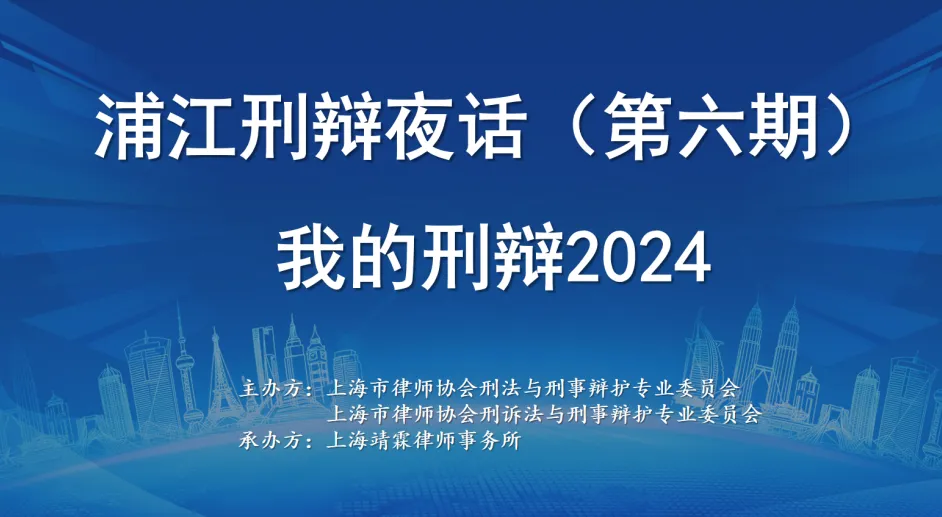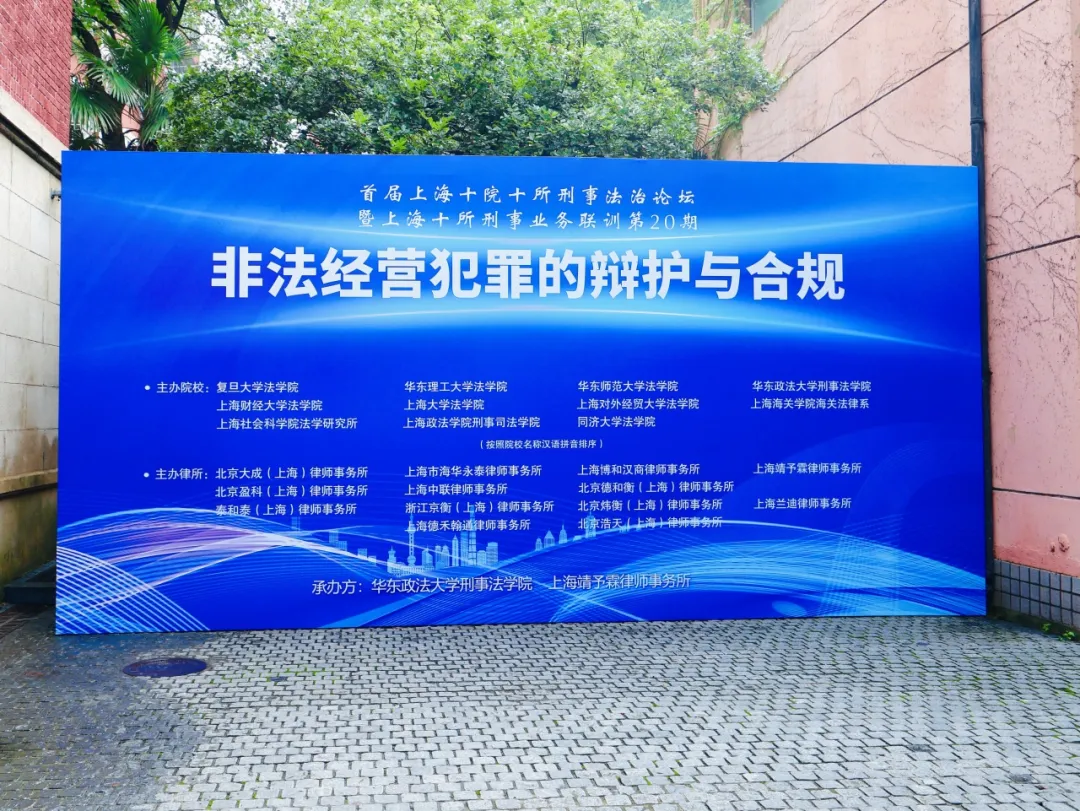2020年8月10日上午十点,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周一例会准时举行。本期例会内容为口才训练,形式为案例沙龙。

内容:近日,张玉环案引发社会热议:1993年10月,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发生命案,张玉环被进贤警方锁定为嫌凶。1995年1月26日,南昌中院一审判处张玉环死刑。经过20多年申诉,2020年8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张玉环无罪。


此次例会有10余位律师参与了本次口才训练,田曳、马贺、程军、刘笛、孔祥君及洪凌啸等从案件细节、审判思路、特殊时代背景、刑罚理论和类案在犯罪细节上的处理等多角度展开。深入案情、分析制度、旁征博引、说理充分。律师们在本次沙龙中展现了独到的见解和雄厚的理论功底,为重新思考张玉环案件的制度得失和社会影响提供了新视角。其中,蔡勇律师的发言对案情分析尤为透彻,即注重细节又把握宏观背景,发人深省,被评为本周最佳发言人。

最佳发言人蔡勇:
张玉环案三个思考:
一是张玉环案发生1993年,联想到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杜培武案等近年来平反的冤假错案,均发生在90年代,那么为何这些冤假错案会集中发生在90年代,与我们那个年代的刑侦技术水平、刑事政策、刑事诉讼理念有什么关联?
二是为何冤假错案的平反如此之难?张玉环从一审被判死缓之后,一直都在申诉,那为何直到判决25年之后才得以平反?这让我联想到以前曾经读过的一本书,美国前检察官吉姆佩特罗所著的《冤案何以发生》中,列举了导致刑事冤案发生的八大司法迷信,正是由于司法迷信的存在,使得冤案的平反困难重重。同样,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有没有类似的“司法迷信”?
三是作为职业律师,如何为冤假错案平反?张玉环出狱之后,感谢了两类人:一是他的法律援助律师,二是澎拜新闻、红星新闻等媒体单位。正是因为职业律师在2000年之后的介入,多家媒体的跟踪报道,才使得张玉环案的平反峰回路转、终成正果。对于职业律师而言,专业性是他的看家本领。那么,他的专业主要就是体现在对案件证据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细节的打磨上。
通过阅读张玉环案的再审判决书,我们发现,原审据以定案的直接证据---张玉环的供述,在作案地点、方式、工具、抛尸地点等处矛盾点很多,缺乏真实性。在间接证据上,麻袋与张玉环衣服上的纤维虽然同属黄麻纤维,但这不具有同一性、唯一性;张玉环供述的用麻绳勒被害人,但尸检报告并无被害人口角处伤痕的检查,缺乏印证;张玉环左手背的抓痕,公安机关也没有提取被害人指甲的相关细胞组织予以印证;张玉环供述的手掐被害人,尸检报告同样没有检查被害人颈前有无皮下出血等伤痕;还有就是,该案是尸检在先,张玉环供述在后,典型的先证后供,供述的真实性同样值得怀疑。等等这些,直接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间接证据也未形成锁链、形成闭环,无法印证张玉环口供的真实性,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因此,作为刑辩律师,要重视案件的法律适用,更要高度重视案件的证据情况,不但要抽丝剥茧分析证据之间的细枝末节,还要从整体上判断证据体系是否能得出唯一的结论,从而在代理刑事申诉案件中做到专业、细致、审慎,更好地维护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

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孙建保作总点评:
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加之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曾经做过与刑事冤错案件相关的课题,所以对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感触,着重想说两点,一个是“看”,一个是“做”。具体来说,对于当前频繁报道的刑事冤错案件,第一,作为法律人,我们该怎么看?第二,作为刑辩律师,我们该怎么做?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目前频发的刑事冤错案件。冤假错案,看起来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案,但在案件背后毁掉的往往是一个人的一生,乃至彻底毁掉一个家庭,所以几乎人人会对刑事冤错案件咬牙切齿,深恶痛绝。确实,刑事冤错案件让人愤怒,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作为法律人,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在愤怒之余,还应该比其他非法律从业者多一份理性。在今天的沙龙过程中大家不止一次提起,为什么当前的刑事冤错案件差不多都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应当说,刑事冤错案件的成因非常多,但时代背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面临的社会治安局面以及刑事司法政策跟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实行的是“严打”刑事政策,追求“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命案必破”的要求也给公安机关带来了相当大的工作压力,并且当时刑事司法实践的规范化和精细化也要远逊于今天,对程序的重视也远不如今天。当时办案还有“两个基本”的提法,不能搞“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大家留心点就会注意到,南昌中院当时的判决书采用的就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这种表述方式,这一点在江西高院判决张玉环无罪的判决书中有记载。现在的司法状况和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相信刑事冤错案件会越来越少的。 或许大家好奇,想知道国外的刑事冤错案件情况如何,推荐大家看几本台版书,《法官的被害人》(这本书在大陆也出版了,书名为《失灵的司法》)、《冤罪》《误判》《流浪法庭三十年》等,大陆近年来也出版了不少直接反映或者间接涉及域外刑事冤错案件的译著,例如《错判》《法官因何错判》等等。读完这些书可以发现,域外的刑事冤错案件一点儿都不比我们少,有些错得甚至比我们离奇得多,离谱得多。日本的“足利事件”、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美国的“中央公园慢跑者案”,我国台湾地区的江国庆杀童案等等,每一起都错得让人瞠目结舌。应当说,刑事冤错案件是个世界性话题,以人类当前的认知能力以及司法智识,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种司法制度能够绝对地避免冤错案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将发生冤错案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另外,张玉环这个案子虽然不幸,但也并非一无是如,例如,不像早期平反的那些冤错案件,需要“真凶再现”或者“亡者归来”,这个案件是直接以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这里折射出的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再如,这个案子平冤的速度比较快,相比于此前的许多案件即便是发现可能有错了也往往要经历多年才后才能沉冤昭雪,本案平冤速度堪称迅速。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真的有冤错案件当事人家属找到我们了,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对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三个问题,“愿不愿做”、“敢不敢做”、“能不能做”。首先,我们愿不愿意去代理这类案件。一方面,这类案件几乎都不会有什么经济回报,当事人家属无一例外地没有支付能力,并且这类案子往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可能努力多年都不一定会有结果;另一方面,代理这类案件,过程往往比较曲折,很容易与当地办案机关发生不愉快。其次,我们敢不敢去代理这类案件。我这里说的“敢”是针对我们律师自己而言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底气能把案子做好。最后一个是我们能不能去做好,就是说如何去做的问题。就怎么样去做这个问题,怎么样从宏观上把握证据体系,怎么样从微观上发现漏洞,这些都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磨练以及高度的责任心才有可能完成的。空有一腔热情,没有过硬的技能,没有好的方法策略,是很难实现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