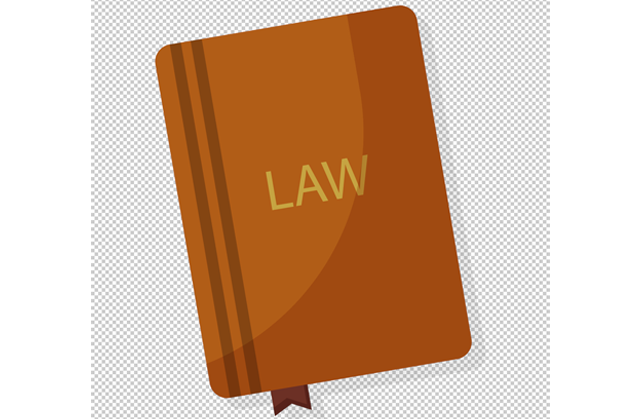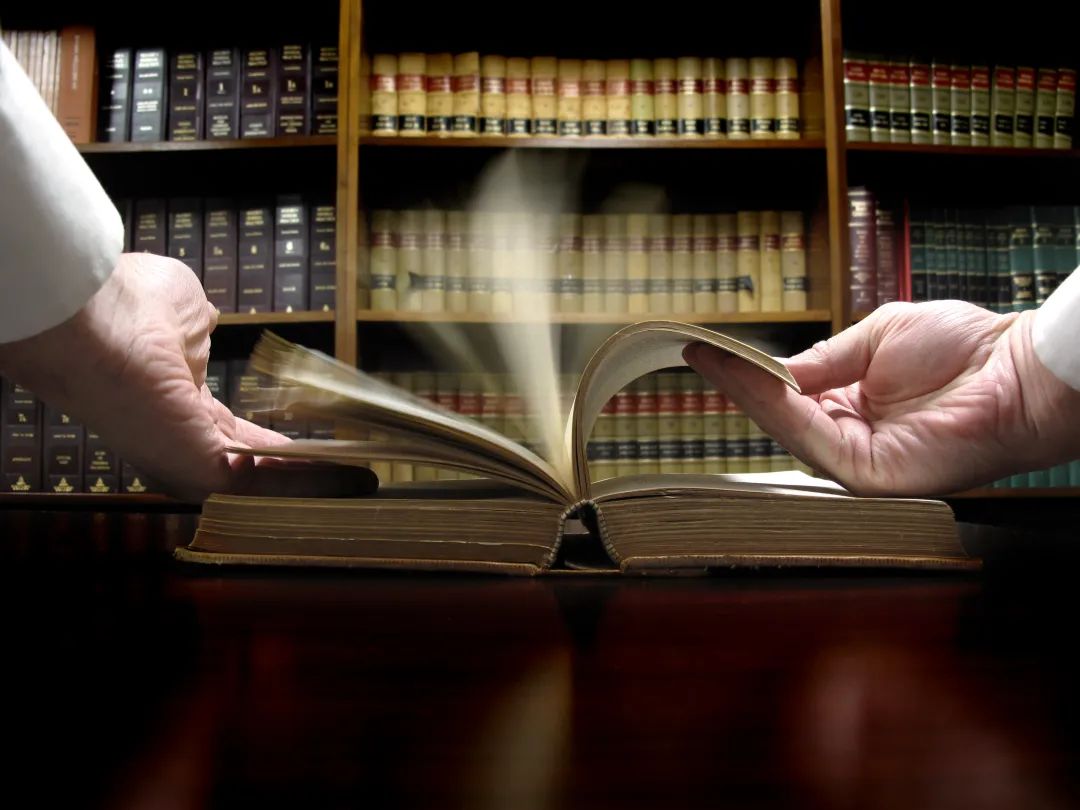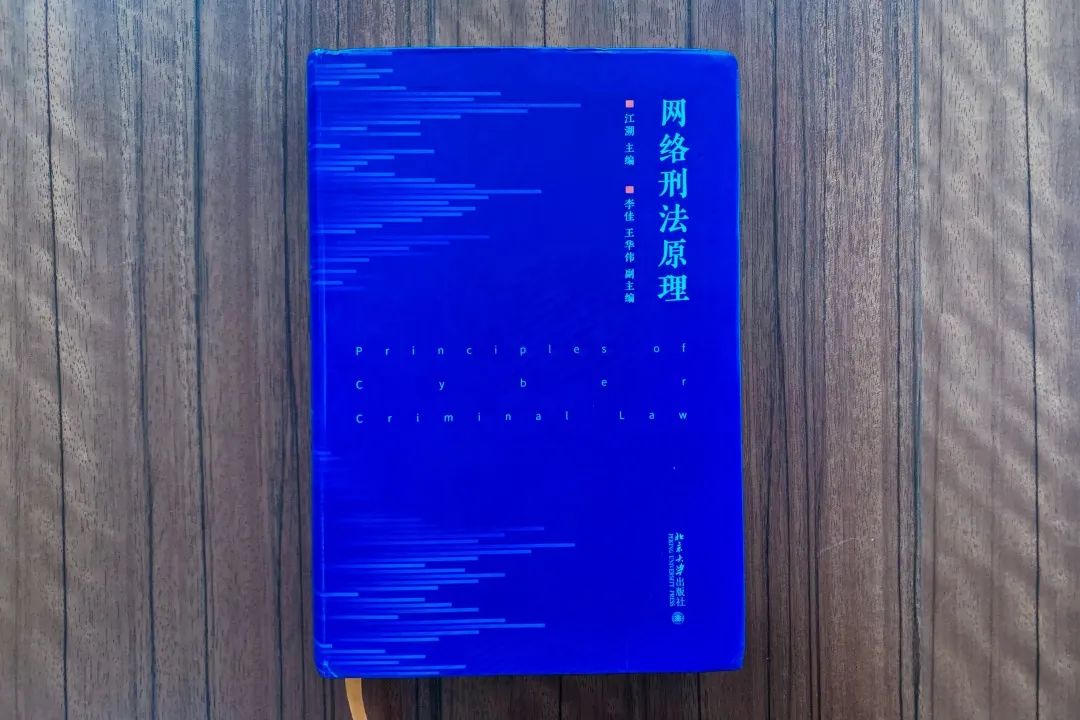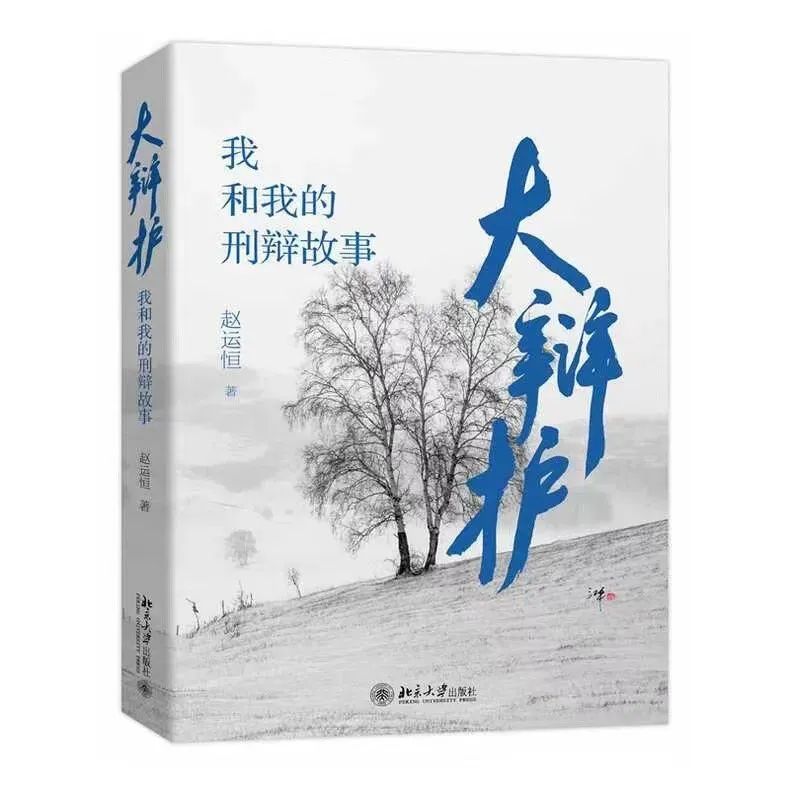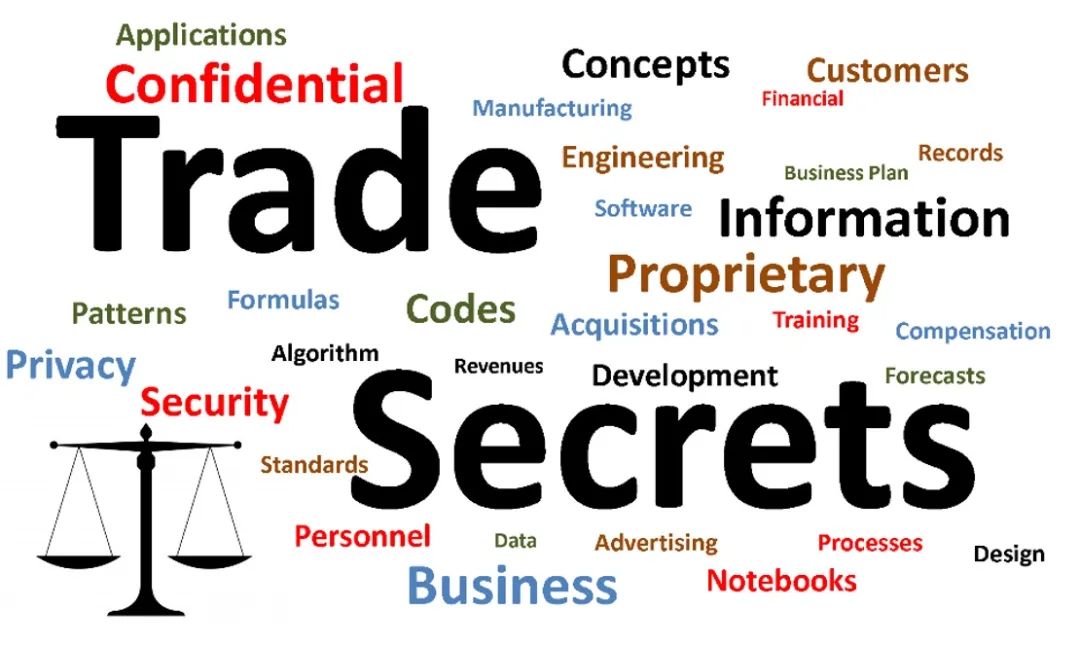从2020年的最后一天回望,在这个疫情暂停了中国社会一个春天的特殊年份,一个暂停在学界探讨阶段数年之久的法律热点问题终于在秋日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围绕在“合规”一词周围的不再是“美国”、“英国”、“法国”而是“深圳”、“舟山”、“上海”,不再是“暂缓起诉”、“不起诉”而是“检察建议”、“附条件不起诉”。
企业合规治理将走向它在司法实践中摸索前行的新一年,在此继往开来之际,笔者有些期许也有些担忧;有一些问题,但没有答案。涓滴杂念汇成一文,向诸位读者方家、也向2021年求教。
一、合规治理的价值
合规治理的“利”在今年的锣鼓喧天中已经被反反复复述说。这里谈四种: 其一、作为行政处罚的抗辩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事由。实务中达成这一效果又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将企业的合规措施作为实施调查和处罚的“酌定情节”,即将企业的合规治理情况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参考因素。这种思路的特点是不需要专门的制度和法规支撑,能够普遍适用于任何类型的行政处罚案件之中。但缺点是合规治理的价值不能得到凸显,可能像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不可靠。而且也会导致“类案不同判”的遗憾。如此一来,法律的指引效果和预测效果就会受到影响,企业对于“不可靠”的治理工作,也就缺乏信心的热情。二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的“经营者的工作人员进行贿赂的,应当认定为经营者的行为;但是,经营者有证据证明该工作人员的行为与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的除外。”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高级官员的权威解读,恰当的合规治理可作为此处但书规定的除外事由。由此,经《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首创,“严格责任-积极抗辩”模式的对企业合规治理的行政激励得以在我国确定下来。此种思路的特色是合规治理的价值一目了然并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公之于众,无论行政机关还是企业都能够清楚认识有无合规治理或合规治理是否得当对于商业贿赂案件处理的影响。企业合规治理的价值得到直接彰显并且非常可靠,能够吸引企业投入成本进行相关工作。遗憾之处则是目前仅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于反贿赂问题确立了“严格责任-积极抗辩”模式,在诸如数据保护、劳动保护、融资贷款等亟需大量合规治理工作的领域还需要等待立法。 其二、作为刑事处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辩解或无罪、不起诉的事由。由于我国(之前)没有相应的刑事法律制度规定,将企业的刑事合规努力作为刑事案件不追诉、不处罚的事由或从轻、减轻处罚的辩解都需要另辟蹊径。稍微展开些讲,大致有以下三个办法。一是利用我国刑事法律一贯坚持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以恰当的刑事合规治理工作作为认定企业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意志的事实基础,从而否定单位犯罪。但问题是一则各地司法机关对刑事合规工作的态度不一定相同,是否作为否定企业主观过错的依据可能产生不同处理。二则一旦否认单位犯罪,就要认定为单纯的自然人犯罪,被告人将面临更严峻的刑事处罚。而被告人有很可能是单位的负责人或高级管理人员,如此刑事合规就在单位与单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之间人为地制造了对立。削弱企业决策者实施妥善合规措施的决心。三则我国刑法传统上以单位成员的意志推定单位意志,不承认单位具有单独的意志,故采取此办法还需要刑事法律理论的革新。二是将企业的刑事合规工作情况视为反映企业主观恶性、认罪态度、社会危害性、再犯罪危险性等问题的因素。从而在决断是否起诉、是否定罪以及量刑时予以考量。这样的办法同样是建筑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上,空间有限的同时也可能因为承办人员的看法、认识不同导致“同案不同判”。三是借鉴英国法律、法国《萨宾第二法案》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经验,建立“严格责任-积极抗辩”模式,从“对预防犯罪存在过失”的角度对企业课以责任的同时也给企业一个通过刑事合规自证无罪的生路。不过这种办法的困难是我国刑法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拒斥“严格责任”。

其三、除了在承受处罚时获得“减让优惠”外,合规治理还具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经营效率的方面。这在刑事责任问题上尤为突出。现代社会分工高度精细化、专业化,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刑事司法工作者作为法律专家,对其他行业的模式、技术、惯例、特点等方方面面不可能有深入细致的了解,更不可能及时更新知识,跟上其他行业的发展变化。由此,当司法人员以刑事法律的严厉目光审视其他行业的行为时,产生模糊和误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不同行业从业者群体间深厚的“技术壁垒”,企业经营者与司法工作者间的“沟通澄清”也必然困难重重。再考虑到现实当中不幸仍未能完全消除的司法恣意和司法专横,由刑事司法人员来“审查监管”企业是一件成本很高、风险很大的事。因此,由企业自身来进行刑事合规治理工作就是由比司法机关更懂环境、懂企业、懂员工的“行业专家”来监管和应对企业经营相关风险,既有利于提升监管水平,更深、更细、更早发现问题,又有利于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监控和处理问题,实现刑事风险防控效果、效率、效益全面提升。
最后、除了经营成本的节约,企业合规治理甚至可能带来直接收益。因为“合规经营”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坚实的“壁垒”。按照合规治理的要求,企业不仅自身要合规经营,还应该对供应链上下游提出适当的合规要求,追求构建全产业链的合规经营环境。倘若这一图景得以实现,就如同全行业对腐败、贿赂、垄断等不正当行为产生了“群体免疫”,能够大大压缩“带病”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附随的效果是,无力承担“合规成本”的企业将被排除在主流市场之外,或者说尚未达到合规要求的企业欲突破“合规壁垒”加入主流市场的成本将大大攀升。类似的现实例子就是欧盟《GDPR》中的白名单制度。《GDPR》对数据跨境流动的条件之一是对方国家对于数据保护的水平不低于《GDPR》的要求。因此,在“一定保护水平之上”的国家中的实体进行数据交换成本降低,而“未达一定保护水平”的国家中的实体进行数据交换的成本则会猛增。由此,一种新的“贸易壁垒”得以形成,其中企业将受到保护,获取收益。
二、合规治理的挑战
然而横梗在企业合规治理的种种果实之前,还有大量令人忧心的问题,除了上节第一、第二点提及的需要进一步的法律理论创新和制度供给外,这里再主要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提示一些困难。 第一个大问题是合规工作会让企业失去什么?最直接的当然是为合规而花费的金钱——包括合规工作人员的薪水、外聘专家的顾问咨询费、合规工作展开所需日常经费等等。但是,哪怕如同西门子花费数亿美元,(对于相应的企业规模、经营规模而言)这只称得上“小钱”。肯定不是合规工作给企业造成的主要“损失”。真正的沉重打击是高标准的合规要求将在当下的时点立即削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或监管不成熟的灰色市场,“主动合规”所带来的短时间内竞争力的下降可能不是“未来的长期利益”所能抵消的。在“剩者为王”的强竞争环境,存活和抢占市场可能是一切所谓“未来”的基础。只有“强者”才有未来,才有余力实施高标准的合规措施,甚至通过前述“合规壁垒”获利。 更进一步,考虑合规水平较高的“文明市场”,合规工作带来的(某些本就不应具有的)竞争优势下降可能是可以承受的。但是这也意味着违反规则所能带来的相对优势也会激增。当这种相对优势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只“有毒的鲇鱼”终将搅乱原本成熟、文明的“生态系统”,甚至可能迫使全行业重新回到恶性的“丛林竞争”之中。 这一悲观图景或许进一步揭示了我国目前刑法对于单位犯罪处罚的一个遗憾:仅有罚金一种刑罚(当然,查、扣、冻企业资产也是一种实质上的处罚,但这不影响后续的陈述)。而“罚金”是可以转变视角视为“非法经营的成本”的。只要上述“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的收益”超过“罚金”,那么企业犯罪在财务报表上就是“划算”的——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对抗的手段(之一)就是加入“资格刑”,取消上市资格、禁止股权交易、取消特许经营权、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是一定时间的市场禁入等。只有这种“一击致命”的处罚,才可能抑制企业突破合规经营的冲动。

第二个大问题是适当的合规治理被认为是可以切割企业责任和员工个人责任。通常这被当然地视为一种合规对企业的“贡献”。但事实一定如此吗?员工与企业在严重的合规事件发生时会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例如刑事调查启动时,相同的犯罪情节被认定为单位犯罪或个人犯罪对自然人的处罚会有明显差别)。以合规为由切割单位和员工责任可能令企业免于处罚却令员工受到更重处罚,这可能挫伤员工士气、减损员工的归属感和主人公意识,导致其工作表现变差。
同时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不合时宜地)“讲义气”的价值观并未完全得到合理看待,企业弃员工不顾的“甩锅”行为可能在实际产生打击企业形象的效果。这与“合规经营”给企业带来的正面形象相互竞争,最终社会评价提升还是降低存在变数。再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误区也尚未完全消除,企业主动揭发员工的违法行为,可能遭到心怀落后观念者的质疑。在这种尚待革新的文化氛围下,“有能力”、“搞得定”的企业可能选择通过“保员工”来保全自身的颜面甚至变相激发员工“大胆地”为企业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合规治理目标至此将完全落空。
最后谈一个常谓之“互联网企业”的特色问题。高水平的数据保护和反垄断经营可能在某种特定角度下与所谓“互联网商业模式”存在天然矛盾。“互联网企业”的一种典型模式即以提供超低价甚至免费服务作为“对价”(或曰“诱饵”)获得数据,再通过数据加工、数据挖掘或其他方式进行数据变现或者通过占据优势市场份额后利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甚至形成垄断牟利。但数据保护和反垄断将阻碍变现过程,使得整个商业模式都变得更困难甚至不可行。另一种方式是积累用户后进行流量变现,但这一则失去了数据分析带来的“精准性”,重归“大水漫灌”的粗放式经营,属于降低企业竞争力的“自废武功”;二则为了“大流量”就可能需要“下里巴人”、甚至需要“庸俗化”,实施所谓“带节奏”、“恰烂饭”等行为,属于“自甘堕落”。
行文至此已经是2020年12月31日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但企业合规治理的发展不会“休假”,它将在这个和下个日升月落间都快步前进,笔者谓之“摸着石头冲过河”。在祝福新的一年的同时,也祝福企业合规治理尤其是刑事合规工作不断克服挑战、彰显价值! 作者: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 、辩护技能研究部副主任、辩论队教练 刘笛